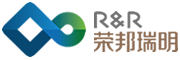
上一篇我们谈了城镇化投资过程中的三类假机会,这篇文章我们沿着这个话题继续深入分析,谈谈第一类假机会背后的逻辑问题,再寻求破解之道。我们先讲逻辑是因为在现实工作中,确实常常有投资人对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直接找到哪条政策可以适用,策划什么概念能引起市场兴趣,设计一个模式就可以运作,一句话越简单明了越好。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很多政府领导和投资人都喜欢“直奔主题”,喜欢简单粗暴的逻辑。实际上真的这么做了,会发现要解决了甲问题,又冒出来乙问题,或者环环相扣,或者没完没了,不禁会让人产生疑问,到底有没有解啊?
这本质上是一个认识问题,成熟大城市周边的假机会制约的是本地的发展,而它从来脱离不了历史,现在的发展是过去努力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的结果。同时,历史也造成了当前的瓶颈。所以,如果不能清楚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走到现在,就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城市化过程的全国逻辑
我们讲到第一类假机会,是资本在进入城镇化投资项目的时候,找不到入口,项目就在眼前,却被各种错综复杂的政策和历史问题所阻碍。大家不免有个疑问,城市化不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过程吗,为什么这么复杂?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城市化的逻辑来回溯一下。
一般我们谈到城市化或城镇化,脑海中会产生出几个共性现象,农民转市民,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建设用地,农村的低矮平房变成了高楼大厦,农业劳动者转业做产业工人。这一逻辑没有错,但是个宏观逻辑。
实际上,这一逻辑是建立在国家层面的法律基础上的,它至少包含户籍管理、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社会保障等若干体系,但站在开发角度土地和规划是做事的基本支撑,所以每个投资人都知道,城镇开发项目实施前,必须有个清晰的规划方案,要通过征地拆迁完成土地集中的过程。
站在城市或政府的角度,谈城市化率的提高,就要以人为核心,通常分两种实现形式来看:
一种是人口的迁移。比如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就业,农村户籍转城市户口,或者是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城务工,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里,无论户籍在哪,计算城镇化率时都被当作分子统计进去了,总体上是全国“一盘棋”的过程,与我们谈一个具体城镇开发项目如何落地关系还不是很大。
另一种就是本地原住民的城市化,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随着城市扩张,从农村变成了城市,人口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我们谈的成熟大城市周边的假机会涉及的政策和历史问题主要发生在这一种。
城市化过程的地方实践
全国逻辑到了地方,就有了充满变化的地方实践。这些变化主要围绕着人、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就每个要素又可以细分很多条具体线索,就人而言,至少包括就业形态从传统农业转向都市农业,由农民转向产业工人,身份特征从农户转为居民;就土地而言,其用途从农用地变更为产业用地、服务业项目用地或是城市景观用地等,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实际占用从原使用权人变为新项目投资人占用;集体经济组织从初级的村集体组织转向股份合作社甚至股份制公司。
围绕核心要素的众多线索变化互相关联,拔出萝卜带出泥,但又各自有独立性的在演化,并不存在一个变了其他必然跟着变的情况。越是在中心城区带动力强的核心城市,各要素演化起来越复杂,有的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先走了一步,有的村镇土地走先了,有自下而上从村镇层面自发产生的,也有自上而下由城市政府主导的,五花八门。
同样是这几个要素的转变,为什么各地又会有差异呢,这就与每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和地方主政思路有很大的关系了,这里拿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举例来说明。
在北京,导致一个村镇发生人口和土地变化的渠道很多,不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北京是首都,很多外省单位和央企都想在北京有一席之地。所以以前在郊区因为单体项目选址落了很多项目,而且往往都是征用农田,这样一部分人上了楼、转了居。但村子还在,没上楼的村民可能依靠着这些单位带来的交通设施和人流建起了大饭店,搞起了娱乐场所,这些人还是村集体组织成员,后来再拆迁时政策就变了,补偿标准提高了,原来的人不干了,都是一个村的,我的地当初被征了按照老政策作贡献了,要不是征,我也可以搞服务,而且干得更好,应该给我补的更多。这种情况很常见,自上而下城镇化由于政策线先后顺序不同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也有自己的故事。政府做了一个指导未来二十年的城乡规划,我这个村子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了,按照规划实施的逻辑,大家都知道这里最终是要被拆迁建成城市形态的,可政府一时半会儿也拆不到我这儿,我不能干等着啊,我也有发展权。现在这地还是我村集体自己的,于是村集体组织大家按照新农村政策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先自我改造一下,搞点集体经济,搞得不错,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等城市规模扩张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傻眼了,按照现在的产值,拆迁补偿金额吓死人,谁也补不起,规划肯定是实施不下去了,于是拆了建的城市化逻辑就断线了。
深圳则是另一种逻辑,作为经济特区,曾经有两轮大规模整体城市化试验,把大量的农民一次性的变为城市户口,身份转变这条线索先走了一步。但土地的实际占用变化没那么快,农民转变来的新市民就业转变也没那么快,大家的心理转变也没那么快,政府管理又不严格,农民就还按照农村逻辑来搞建设,种房子,后来搞城市建设,探索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又需要去解决很多历史问题。这是身份转变线索先行了一步,但其他线索跟不上,还按照老逻辑发展导致的城市发展瓶颈。
所以说,由于大法和小法逻辑,各地在改革开放和核心政策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又做了很多探索性试验,城市化大逻辑落到每个具体的城市,就产生出了复杂的地方逻辑,上海有上海的探索,天津有天津的试验,成渝有成渝的新思路,没有哪个城市的逻辑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不留问题,只是因地制宜的找到一些突破点,有搞成功的案例,一定也有不成功的经验。
政策创新需要新的整合逻辑
现在很多投资人搞城镇化往往是找不到投资入口,就是因为地方逻辑在自然发展中走不下去了,现实问题往往比上文中描述得要复杂得多,要破解这些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新的逻辑,即不违背国家政策的大逻辑,又不否定地方的小逻辑,还要让卡壳的地方能够继续运转下去,这就是政策创新的难点所在。而投资人面临的难题就是,这些问题要依靠政府,可政府破解完了难题,投资机会又不是你的了,谁来都能干了。
讲破解路径首先有个前提,就是未来的城镇化政策,一定不是在国家层面的大逻辑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能是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国家政策创新基础上更灵活的运用,才可能真正破解具体问题。其实,国家层面也从来就没专门提过什么城市化逻辑,从上文分解出的各种要素就可以看出来,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最终只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才是政策创新的本质出发点。
而面对这些地方逻辑在自然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地区或项目,首先要理解大部分地区在过去是有动力的,但由于某一要素单线的推荐,造成了在人口、经济、土地、集体组织等方面全面实现城镇化的停滞。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之所以投资人没入口是因为再往下走城镇化的动力不足了:有的农民已经上楼了,但宅基地没有拆,农民把宅基地上房屋都出租出去,再想拆就很难了;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很好,每月给农民的补助甚至远高于城市养老保险给的标准,那么他也就没有了转居的动力;还有的村甚至按照城市建筑标准建起了大型专业市场,全市知名,每年产值丰厚,再想整体改造也就难了。
因此,为了推进城镇化,政府要想法恢复这些地区的活力,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一些,前几年北京市推行过城市结合部重点村的改造工作,我们的团队在帮助政府梳理和研究这些村庄出现的问题时,找出一些特征不同的典型例子,从建国之初开始研究这些村子的发展过程,把上面的各种要素变化梳理出来,可以看到每个村子发展的脉络都不一样,需要破解的现实问题也不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资金投入来推动,每一类问题应该由谁来出钱,以什么形式出钱,与财政是什么衔接关系,与金融资本是什么衔接关系,与原来政策是什么关系,原住民、村集体和企业都能得到什么,大家有没有动力来支持,谁来干比较合适。就是试图在一个小区域里面,封闭的去考虑城镇化各条线索的演变,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城镇化各项问题的路径,从核心要素演进的单线逻辑转变为围绕项目的统筹逻辑,再通过投融资去整合平衡,让传统路径走不下去的城市化过程走下去,这就是政策创新。这种创新无法以公开发布的形式出台普适性政策,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却比明示的政策更有效。
在创立和推广投融资规划方法过程中,经常有人建议我们把投融资规划方法标准化,我们也在尝试做这项工作,也产生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但我更愿意讲系统工程,更愿意把它定位成一种整合方法,因为投融资规划本质上是要解决城乡规划实施过程中资本如何落地的问题,需要破解复杂的具体问题,只有整合才能解决真问题,把假机会变成真机会。
版权所有: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