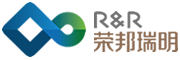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并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并由此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深入下去,这次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关键词:价格、工资改革
改革背景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一直偏低,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负担,要加快经济建设,必须进行物价改革。
根据对1979年底的经济研究,当时的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悬殊。
从1979年到1984年,国家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主要是调整价格。即通过行政手段来提高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
1979年春夏,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8.3%;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即基础产品价格提高,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提高,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此次调整没有解决价格扭曲的问题,却使价格水平提高了。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然而,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有很大的风险。为了使改革稳妥进行,国家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
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价格“双轨制”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目的是在价格形成上逐渐转入市场机制。“双轨制”的实行,一方面可以保证国营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的优势,同时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使非国有经济获得了生存空间,曾一度给经济生活带来了生机。
但是,在生产资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也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计划内物资在市场出售,但是在高额的经济利益面前,“倒爷”应运而生了。他们通过有政府背景和资源的人或公司,以计划价格买进,然后再按市场价格卖出,从中赚取高额差价。政府对国企,城市居民的补贴,相当数量落入此辈的口袋里。有经济学家保守估计,他们每年赚取的价差是1000亿,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6%-7%。
权力和金钱的恶性结合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1987年9月17日甚至还专门颁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双轨制”下,作为生产厂家,会趋向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并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范围内的合同不能完成;作为用户,趋向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并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
从1985年开始,国内价格总水平明显上涨,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决心。
改革过程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会议情况。李鹏提到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讲道,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1988年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闯关行动”是3月份从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30%之间。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驻地城市每个职工补贴10元,其他城市补贴少一些。
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4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这种做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
但是这一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迅速蹿高。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物价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过程中,某些人的利益暂时受到一些影响,最终总是会得到解决的。
原本为了“打预防针”的媒体宣传,无形中却加重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放开以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发不可收,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回忆:“1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蹿到300多块,汾酒从8块涨至40块,古井贡酒从12块涨至70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至十来块”。巨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抢购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这次“价格闯关”波及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
后续改革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改革方案中讲到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同时,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核定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综合零售价,对计划外生产资料严格执行最高限价。重新控制定购粮、议价粮价格,城市大路菜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北方冬储菜、定量供应部分猪肉价格不准涨价。对计划外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规定名烟酒价格的上下浮动率。对所有重工业、轻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国务院“治理整顿”的措施包括冻结物价、收回已放开的价格管理权等严厉手段。
1989年11月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来解决依旧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决定》确定在包括1989年在内的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决定》要求“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1990年先取消煤炭价格“双轨制”,以后逐步增加取消的品种。对于短期内难以取消的品种,通过适当提高计划价格,加强自主价格管理的办法,逐步缩小两种价格的差距。
严厉的治理整顿措施使价格总水平从1989年3月开始回落。粮食价格从1989年7月份以后大幅下跌。到1990年,粮食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出现了谷贱伤农问题。于是,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规定各地向农民收购议价粮时,价格不得低于最低保护价,对其它农产品也提高了收购价。
1990年以后,由于治理整顿与国外的“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摆脱困难的经济局面,决定深化改革,应该放开的价格要坚持放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及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对以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经验。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及以前就存在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以后刺激粮食生产,调控粮价的主要政策措施,调整原油、煤炭、盐、统配木材及铁路等价格,也使这些价格变得相对合理。
总的来说,治理整顿措施过于严厉,导致了经济在1990年的硬着陆,通货膨胀虽然受到抑制,但牺牲了发展。事实上,治理整顿的措施并没有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只是把问题冻结了起来。加上1989年“风波”之后,特殊的国内国际局势,需求大幅下降,问题被搁置下来。
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市场的“姓社姓资”等观念问题。同年10月,“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价格体制改革,进入了创建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评价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此次失利,表现为商品抢购和物价飞涨,它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是负面的,但并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生产崩溃,然而它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对城市的影响
物价、工资改革是我国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型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受到当时物资短缺和生产能力低下等基本条件的制约,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1989年前后城市发展甚至一度停滞。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我国市场价格体制改革,以逐步放开的生产资料市场为基础,城市工业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版权所有: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