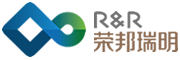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汽车牌照算不算资源,是不是也应该让市场在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Apec蓝给人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人们愿意把这样美好的事物留下,甚至很多人提议,把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来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还北京一个蓝天白云。就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多少是汽车尾气的因素,apec 蓝中有多少是单双号限行贡献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单双号限行,表面上为了还消费者一个蓝天白云,为了消费者呼吸到好的空气,实际上真正的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北京进一步吃紧的交通问题。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问题由来已久,奥运还没有结束,很多人就在讨论单双号限行的常态化,最后不了了之。随着新常态观点的提出,各种变了味的新常态也跟着浑水摸鱼,试图用行政手段,简单粗暴地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其实我初步做了一下调查,支持用行政手段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遇到一个政策问题,就会出现市场解决手段和行政手段之争。用行政手段简单粗暴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样有市场?为什么这种争论的结果往往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而结束?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年的决策逻辑,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问题的解决是硬道理;就业的硬道理推导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导出效率是硬道理;效率是硬道理导出行政手段是硬道理。这样的硬道理确实是无懈可击,确实是硬的不能再硬的道理了。因此这种硬道理大行其道,导致我们决策过程简单粗暴,缺乏真正科学的论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硬道理,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我是积极支持采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的,可是行政手段不是万能的,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还需加以认真分析和论证的。就拿单双号限行这样的行政手段来说吧,也许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我们是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行政办法解决问题的,比如奥运期间,比如apec期间,这些都是老百姓或者说每个城市的消费者都能够接受的,因为这毕竟是国家的大事,让国家把大事办好,不给咱国家丢脸,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但是这种手段常态化之后,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我看未必。那么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站在城市管理者的角度,交通问题的解决,本质是是什么问题?我认为是解决整个城市的道路通行效能问题,整个城市的道路通行效能越高,老百姓满意程度就越高,每个人的出行效率越高,这个城市就处于一种高效能状态。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通行效能呢?就是单位时间内,所有道路上的车辆总共运行的距离,也就是路面车辆平均速度与路面车辆总数的乘积。站在整个城市的角度来看,道路通行效能是城市重要的资源,如果横坐标是路面汽车总数,纵坐标是城市道路通行效能,则通行效能是一条倒u型曲线。
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随着城市交通流量的增加,每个消费者感知的是交通效率的降低,似乎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这是消费者站在个体角度看问题形成的结果,但是站在城市宏观效果的角度来看,与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城市道路规模确定之后,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一段时间内,或者说从交通流量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过程中,道路通行效能并没有下降,而随着通行车辆增加而不断增长。因此站在城市道路效能的角度,这个过程是个通行效能上升的阶段。当交通流量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汽车的通行速度就开始下降,整个城市的道路通行效能就不再增加,而是处于减少的状态。这时城市道路通行效能达到了最高值,道路通行效能就开始下降了。
北京市中心区域,或者说三环以内,基本上处于道路通行效能下降的阶段上,因此北京市在apec期间实现单双号限行,使得单位面积上汽车行驶量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以下,从而使得城市道路通行效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使得很多城市消费者中驾车一族感到很爽,希望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先仔细回想一下北京apec 期间的交通出行状况,总体感觉确实相对比较好,交通效率也比较高,可是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当时是在私家车数量减少一半,公车几乎大面积停用的前提下得到的效果。以APEC期间的汽车行驶数量数据为基础,再增加多少车辆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端,我是没有这样的数据进行模拟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直观地感觉到的,就是离临界点并不是很远,比如说早高峰京通快速进城方向,东西二环南段北向南方向等路段依然处于拥堵状态。当时消费者虽感觉到了交通的便利,但是也不是那么的通畅。也就是,当仅仅启动单双号限行,而没有公车大面积限行的情况下,北京的道路通达效能是不是会严重下降,也就是这种政策本身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假设,实行了单双号限行制度,而且道路通行效能处于上升阶段,那么根据对消费者的研究,这时单车的利用率会出现比较大的提升,同时由于交通便捷度推升,很多过去不想拥有双车的家庭也会进入到双车家庭的行列中来,一般情况下,只要北京的车辆行驶畅通,一定会在短时间达到汽车通行量的饱和,消费者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问题,甚至有的人就是不差钱,宁可交罚款。尾号限行政策刚出台的时候,大家不是也抱着美好预期接受的,可现在运行的结果呢,没有几天,就马上饱和了,结果实在是差强人意。
那么行政手段为什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呢?或者说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只是短期时间内有效呢?这里离不开北京汽车拥有量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说北京汽车拥有量严重超标,这个结论估计没有多少人持不同意见,也就是北京的城市消费者对交通的需求是很大的。用道路通行效能曲线来看,这个汽车拥有量,严重超过道路通行效能最高点。在这样超量需求存在的情况下,无论与你用什么样的行政方法,消费者都是可以想尽办法进行消费的,当你通过单双号等行政手段限行,导致路面汽车处于不饱的状态时,这时道路通行效能没有饱和,市场一定会快速作出反应,达到新的饱和状态,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然而强大的反应和计算能力所决定的。
因此,行政手段通常处于费力不讨好的状态,这是一个人或一伙人的计算能力对抗千万人的计算能力的必然结果。因此聪明的办法就是政府不要做这样的计算,让消费者自己去计算,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什么样的平衡态是大家愿意接受的。
解决汽车拥堵问题,应该通过机制的设计,也就是交给消费者自己来解决问题。这种机制要通过权利的设计和交易来解决,比如可以设计出道路通行权这样的产品,我有汽车牌照,我就有了道路通行权,这种权力是一种资源,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当把权利进行交易的时候,交通问题其实照样得不到根本改变,整个城市交通一直在道路通行效能度最高点这个稳定状态附近徘徊,但是这种结果是消费者自身博弈的结果,当你让渡你的通行权力的时候,你得到了货币的补偿,当你使用通行权超过了一定的水平,你就要为多使用的部分进行买单。应该说,这种设计的结果,有一种均贫富性质的公平在里面。可能也许有人会说,这也不公平,我没买车我还纳税了呢,我照样也应该有路权。这个我也赞同,通行权每个城市的公民都应该有,纳税越多的应该给与的更多。按照这样的机制,汽车限购不应该再用摇号的办法,而应该象上海一样采用汽车牌照拍卖的方式,在汽车牌照拍卖的时候,就给了你路权使用的通量。当你取得了路权通量,你如果不用,还可以反过来通过交易得到补偿,这一方面人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汽车,支持了经济的发展,支持了gdp和就业,同时也在贫富之间创造了更多转移支付,实现公平的路权。
也许市场化解决问题的思路会使得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与我们职场中流行的复杂问题简单化思维有点矛盾。其实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在职场中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是一二号首长的思维,因为到了一二号首长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证的问题,论证的过程是否合理,是否把问题分析的透彻明白,是个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过程,可是问题呈现在一二号首长面前时,就必须把分析过程去掉,这些不是他要把握的问题,而是基层人员要把握的问题,因此一二号首长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是,很多领导没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件事情说明白,致使社会上对这个问题产生很多误解,以至于很多城市的公务员甚至搞不清怎样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变成简单问题复杂化。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决策方案报给一二号首长之前,要把看似简单问题复杂化,搞清楚问题的本质,形成简单清晰的决策方案,供领导决策。简单清晰的决策方案并不是真的简单,是把要决策问题的实质说清说透。用系统工程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这才是一个重大决策应有的程序。
新型城镇化中有很多用限行、限号这样行政思维解决问题的惯例,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都是要改革的。要尝试着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比如京津冀的协调发展问题,如果把发展权进行交易,把青山绿水当作权利进行交易,才能够实现习大大所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解决北京交通问题远不是单双号限行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这里只是抛砖,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多学科协同来解决,是需要一个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
作者简介
李伟: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合伙人,《新型城镇化蓝皮书》主编,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投融资规划方法的创始人。
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开发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政府投融资、城市营销以及政府投资类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及实践,带领其团队在总结各地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投融资规划”方法,填补了将系统工程方法与整合性技术运用于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空白,在多个城市进行实践应用,有效的解决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并打造了在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城发展模式——“长阳模式”,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广泛认同。
先后出版《政企合作——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投融资规划——架起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桥梁》、《破解城市建设困局——长阳模式解读》、《破解城投公司困局——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基因》等著述,发起并主编《新型城镇化蓝皮书》。
版权所有: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